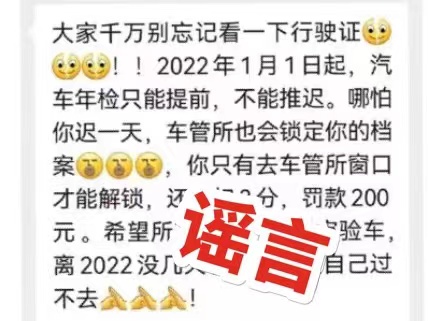从20多年前的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作家陈丹燕和很多铁杆影迷一样,每天苦恼于观影的档期。她在城市的各个影院间穿梭,很多时候,两部电影的时间冲撞了,她甚至要提前离席,晚点入场,掐头去尾地看,才能在捉襟见肘间“雨露均沾”。
今年电影节则有些特别。由她执导的电影《萨瓦河流淌的方向》被搬上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银幕。
 (资料图)
(资料图)
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里,有她多年的书迷;有对塞尔维亚——这个巴尔干半岛上多灾多难的国家充满好奇的人;也有闭着眼睛,抢到啥算啥的电影节开盲盒式观众。
她把塞尔维亚朋友们悲喜交集的生活呈现在中国观众的面前,那些故事细碎犹如中国观众自己的生活,却又厚重强烈到引发人们深深的共情。她依然在城市的各个影院间穿梭,这次不为看电影,而是为了去观察那些走进影院看她电影的新朋友们。
前一阵,严防死守保身家的陈丹燕还是“阳了”。阳过之后,身体倦怠,除了去电影院里看看观众,多数时间她在家里蛰伏着。作为辰山植物园文化园长,一位很多年的植物与园艺爱好者,她将要踏上新的旅途,追寻中国月季漂流到欧洲的故事。
在她出发之前,我们与这位写作超过三十年的作家,57岁的新人导演聊了聊她的书,她的电影,她眼中的塞尔维亚。
上观新闻:您的电影起名《萨瓦流淌的方向》。萨瓦是一条什么样的河?
陈丹燕:萨瓦是个人名,是一位塞尔维亚的圣人。熟悉地理的人会知道这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萨瓦河在贝尔格莱德是融入多瑙河的,但是塞尔维亚这个民族永远融不进欧洲。
上观新闻:您七次前往,这个过程是否存在一个递进的层次?
陈丹燕:有。最早就是对塞尔维亚的历史有兴趣。但是我在上海很难找到中文版的塞尔维亚历史。我读过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那是一本塞尔维亚游记,但这些都不是那种梳理清晰的编年体历史。
后来我知道东正教堂的湿壁画上有很多塞尔维亚的历史故事。一开始我去了很多东正教堂,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人物,从他们的故事开始学习,慢慢进入塞尔维亚的历史。
历史上南斯拉夫在奥斯曼和奥匈这两个特别大的王朝的夹击之下,有非常漫长的战争时期。为了搞清这段历史,我又去了匈牙利 ,维也纳,就是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范围。后来再南下去了土耳其,进行了差不多长达50天的旅程,从地理上的移动,可以明晰地看到历史留存的变迁。
当我再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就会很清晰地知道他们食物的口味是从哪里来的,咖啡的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北部与南部人信仰如此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经过了很长期的田野调查以后,才在贝尔格莱德拍这部电影。
上观新闻:电影中使用独白的方式在网络上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一部分人会觉得作家电影,使用文字和旁白叙事是一种独特的格式,而有一些人会认为这弱化了电影语言的叙事,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议呢?
陈丹燕:我最初想要做这个独白系统,是因为我发现了素材的一个弱点。我无法找到完全体现我的想法的画面。我觉得这是纪录片导演经常会面对的情况。
其实我们这部电影的片比超过了10:1,但我很快意识到依靠画面是不能完全表达我想要的内容。因为拍片的时候我们从摄影机里看到的画面是90度的,而我为写书而展开观察和写作的视角是180度甚至360度的。
镜头也没有五感,拍摄、记录的状态和我为了写书在一旁慢慢安静地感受和观看的状态也是很不一样的,拍摄会遗漏很多很多细节。
写作30多年,我很清楚通感来了会如何促进灵感,把创作推进下去。因此我觉得,拍摄的素材相对文字会缺少一部分的张力。
因此,我对于文字和声音在电影中起到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相信我的读者们可以通过文字和声音,在观影的过程里对于很多内容产生想象和自我的建构,毕竟一部作品最终是由接受者来完成,而非创作者。
但同样的,我也相信影像的力量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的原因。关于塞尔维亚我写了《捕梦之乡》,和这部电影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两者都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且排他的表现方式。
上观新闻:拍一部电影,写一本书,都是非常长线程的工作,今天年轻人都在讨论内卷,似乎很难有条件用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沉下心来创作。
陈丹燕:从对一件事有感受,再到进入创作状态是有规律的 。就像果子,没有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事情还不可控就一定去追求结果,那是你自己想多了,会带来很多烦恼。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内卷是被迫的。如果一个人一直被推着走,那就没有办法成为你自己,这样的人生很痛苦。如果一个人具备一定的条件,还是应该去追求自由。如果一个人不完全被社会或者周围的环境带着走,那可能会快乐得多。
更多时候,人的竞争是内化的,是自己在跟自己争。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什么,然后承认世界并不是围绕着某一个人转的,但这个世界多数时候也并不是一个鬼门关,非要强过别人一头才行。我自己年轻时见过很多一定要强过别人一头的人,花就开了一季,然后就开不出来了。 那些看起来比较“佛系”,觉得“没关系”,“这个事情好好玩”的人,现在好像都还活得挺好。
上观新闻:这让我想到拍电影。相比写作,拍电影十分复杂,导致很多创作者总是面临身处失控边缘的困境,作为一个有“佛系”价值观的作家导演,你怎么处理这个困境呢?
陈丹燕: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克服的。很多很多次真的难得做不下去了。拍电影和写作是一个协同流程上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会发现,我的表达让团队很多时候不好理解,而我也不知道他们想要表达什么。
如果做不下去,那就停一停。我像农民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经历了一个阶段以后收获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获得很多是对创作方法的探索。比如说我一定想去试,具象和抽象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个中间或者灰色的地带。
我从《上海的风花雪月》开始就一直在做图文书,处理图和文的关系,这30年时间的实践让我对图像不陌生。(拍电影)只是让画面动起来了,那当然也会碰到很多新的问题,这种探索的过程本身对我就是意义,有时候遇到瓶颈我就放一放,放个几年也是有可能的,写书也一样。
上观新闻:有做一个好项目直接黄了,或者历史上有一部作品开始以后就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况吗?
陈丹燕:当然,这太正常了。有些项目停止以后,过了几年电脑里翻出来一看,发现问题迎刃而解了。关键是中间过去的这些时间我并没有浪费,那个积累的过程会让路径自己浮现出来。
上观新闻::电影节期间,影片上映以后观众的反响怎么样?
陈丹燕:很好呀,获得了很多的鼓励,每天都很开心。陈保平(陈丹燕丈夫)说:”哦哟你现在不在一楼了,都飘到二楼去了!”
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位观众,是随手买票,走进我的电影场次的,看完以后写,(电影中)到底是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对话,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这句话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还有就是大家都蛮喜欢电影里的塞尔维亚人的。有观众看完以后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现在又开始发生争执,让他联想到俄乌。
我电影里拍到的一个小姑娘,说到她爱一间美术馆,它好的时候,她爱美术馆生机勃勃的样貌;在它一塌糊涂的时候,她爱它颓废中体现的浪漫。
这个观众觉得,电影里这个桥段在表达一个有很多仇恨的地方发生的关于爱的故事,这是他的总结。为故事赋予爱的主题的过程里,我自己是无意识的,但是回头去看,在组织故事时,我在逻辑上又是自洽的,关于爱的表达形成了自然地流露,观众的提醒和我自己经验的相互映射,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收获。
上观新闻:这次电影节你从观众变成了参展导演,对于你来说电影节意味着什么?
陈丹燕:电影节对上海太重要了。我们不像西安这种城市,有那么悠久的历史文脉,而是需要很多大型的艺文活动来帮助塑造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除了电影节,也包括书展,双年展等等。
还有一点是,虽然现在网络流媒体平台十分发达,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新的电影,但是似乎只有在电影节上,才有机会看到很多世界主流舞台以外国家的电影,这对于创作者和观众都是十分重要的经验,人们通过在电影院里观影的方式被更多地连接起来了。
上观新闻: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不免会想,这种巨大的片比和漫长的工艺,其价值毫无疑问,但也会让人不由得想起,今天短视频这种十分轻量化展开叙事的方式。你觉得短视频会成为你的一种创作语言吗?
陈丹燕:我觉得短视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时代语言。我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会有种尴尬的感觉。2个多小时,你要塑造一个特别复杂和完整的人物形象,时间是不够的。
那我觉得一种就是剧集,10集的体量,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叙事,看起来也很过瘾。要么就非常短,几分钟,这种就像19世纪的短篇小说,20世纪初的微小说,都可能出非常好的东西。但要求构思能力更强。
如果觉得短就好糊弄,那其实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难写多了。一个短视频因为它短,容量可以做得非常的饱满,看完以后人会愣住半天回不过神,里面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栏目主编:张春海
文字编辑:蒋迪雯
本文作者:董天晔
关键词: